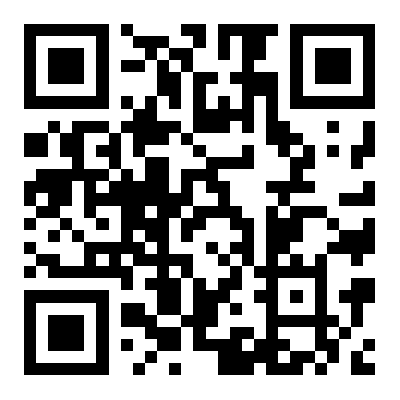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作了第四次重大修訂,增設缺席審判程式,填補了刑事訴訟制度法律漏洞。為有效地打擊貪污腐敗犯罪,加大境外追贓追逃,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故意規避法律制裁,確保法院及時有效地作出司法裁判,維護國家司法權威,舉足輕重。但內地《刑事訴訟法》僅用一章七條的篇幅規範缺席審判程式,過於簡單籠統,如何保障刑事缺席審判制度得以有效適用,是值得關注的焦點問題。而刑事缺席審判證明標準設立是否科學、合理,直接影響證明活動的開展和訴訟程式的進行,進而影響法律的實施效果。目前,刑事缺席審判仍沿用“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不僅缺乏可操作性,制約該程式的運行,更限制了其犯罪控制、追贓追逃功能的實現。
一、刑事缺席審判程式設立之初衷
(一)打擊腐敗犯罪與強化追贓追逃
政治腐敗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是最嚴重的腐敗,懲治和預防腐敗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國家治理難題。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四十餘年,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多,物質利益刺激的增強,公職人員腐敗案件發生率高位運行。一些腐敗犯罪分子攫取巨額公共財產,為規避法律制裁而逃至國(境)外,變換身份並將涉案財產藏匿、轉移至國(境)外。如許超凡、許國俊等人貪污、挪用公款金額達4.82億美元,其利用假護照逃往北美,並通過洗錢方式將贓款轉移到美國等地。因中美兩國缺乏引渡條約,二人最終在美國被審判。此外,囿於“死刑犯不引渡”、“政治犯不引渡”等國際公約或慣例的限制,引渡外逃貪官回國接受法律懲罰難上加難。截至2017年3月底,我國內地尚有涉嫌職務犯罪外逃出境的國家工作人員365人,加之失蹤不知去向的國家工作人員共計946人①;截至2020年11月,仍有40名“百名紅通人員”未歸案。內地刑事訴訟法專門針對貪污賄賂等犯罪確立缺席審判制度,既體現了國家對腐敗犯罪“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決心,又能及時有效地追訴犯罪,強化境外追逃力度,加大對腐敗犯罪分子的震懾,維護法律的尊嚴與權威,減少並預防腐敗犯罪的發生。
(二)司法公正與效率之平衡
公正與效率是法律追求的價值目標,面對訴訟成本高昂、案件積壓嚴重、司法活動拖延的難題,世界各國不外乎通過科學配置有限的司法資源與合理設計訴訟程式等方式解決。當然,刑事訴訟程式的運作不僅具備經濟合理性,還應實現訴訟效果的合目的性。即訴訟結果的實現符合公正、秩序和自由的價值目標。故公正與效率有競合,義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曾說過:“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②未設置缺席審判程式之前,因被告人長期脫逃致使訴訟程式無法進行時,只能中止,訴訟程式停滯不前,案件久拖不決,不僅無法實現懲罰犯罪的功能,還會造成司法資源重複投入,降低訴訟效率。如百名紅通人員頭號嫌犯楊秀珠,曾3次向美國申請政治避難,歷時14年竄逃6個國家。為遣返楊秀珠,內地檢察機關與美國司法執法部門進行多次交涉,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另偵辦貪賄等腐敗犯罪案件時,言詞證據的準確度會隨著時間的拖延而逐漸下降,對此類案件適用缺席審判,有助於監察機關準確查明案件事實,保證有罪的人及時得到法律追究,追求效率的同時實現刑罰威懾功能,促進司法公正。
二、當前刑事證明標準在缺席審判程式中面臨障礙
內地《刑事訴訟法》長期將“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作為定罪的唯一證明標準,儘管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引入了“排除合理懷疑”,但尚未修改原證明標準,只是從主觀上對“證據確實、充分”作進一步明確和解釋,便於辦案人員把握。③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604條第2款對此予以重申,法院缺席審理,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仍是“證據確實、充分”。腐敗犯罪案件的公職人員往往職務級別高,反偵查能力比較敏銳,此類案件所涉證據收集空間狹小、種類少,監察人員收集的多是言詞性證據,通常缺少客觀證據。即使能夠收集到客觀證據,多為贓款、贓物,無法單獨作為定罪依據。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將現行過於抽象且難以詮釋的證明標準繼續適用於缺席審判程式,該程式啟用障礙較多,直接影響程式的有效運作及目的實現。
(一)缺乏可操作性
證明標準是衡量對案件事實的證明能否達到法律所要求的水準和程度。在刑事訴訟中,檢察官依據該標準審查證據,以求達到己方主張,而法官依據該標準判斷公訴機關是否完成了訴訟證明活動。作為標準與尺度,總是越具體、越清晰、越精確,就越容易操作和把握,但遺憾的是證明標準卻不具有司法人員所希望的精確性。④職務犯罪案件的調查模式是“由人查案”,不同於一般刑事犯罪“由案查人”的偵查模式,加之賄賂犯罪隱蔽性較強,缺席審判程式中被調查人供述的缺失增加了案件證據材料的獲取難度。當前,缺席審判的證明標準與一般刑事案件無異,“確實、充分”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應達到什麼要求,無法用精確的數字進行界定,法條本身也無法給出答案。不同主體在不同時空對事實、證據的認知不同,必然導致不同評價結果。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下,若無法將司法人員的主觀判斷客觀化並轉化為可操作的規則,必將不利於犯罪事實的查明,尤其是賄賂犯罪,被告人供述缺失,即使有行賄人證言,也只能認定受賄人收受財物的事實,法官如何認定其具有主觀故意,目前的證明標準無計可施。
(二)程式啟動困難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缺席,仍要求案件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同時達到“證據到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並具有唯一性”的標準脫離實際。有學者擔心,一刀切的高標準和嚴要求可能不符合辦案的實際情況,在被告人缺席的情況下,許多證據難以有效核實,在未開庭的時候就要求達到這一標準,是非常困難的,甚至可能導致該程式無法啟動。⑤《2021年最高人檢察院工作報告》中,對潛逃境外19年的貪污犯罪嫌疑人程三昌適用缺席審判,⑥系首次啟動該程式,也是目前唯一一起適用缺席審判的貪官外逃案件。犯罪事實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檢察機關才可啟動缺席審判程式。貪賄犯罪案件言詞證據居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場,基於案件事實的不可逆、取證方式合法性及現代科技水準的限制,審前調查取證過程帶來的拖延,不僅加大了證據滅失的風險,還會阻礙程式向前推進。這勢必影響打擊腐敗犯罪、追逃追贓的實際成效,也會削弱刑罰的威懾功能。
二、多元化證明標準之構建
訴訟的目的在於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定紛止爭,對過去已經發生的事實進行重現體現為證明的特殊性,是一種逆向求證過程。基於人類理性的有限性,裁判者對已發生的事實未親身經歷,不可能得出絕對無誤的認知。法官對案件事實是否成立進行判斷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受法律觀念、經驗等因素的影響,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性色彩,包括證明標準的運用。在同一訴訟中,隨著程式的深入,對證據、案件事實的認識和掌握程度應是階梯型結構,這樣才符合案件真實層進式的發現規律。故應針對不同的訴訟階段、不同的案件事實設定多元化、多層次性的缺席審判證明標準。⑦
(一)不同訴訟階段的證明標準
1、程式啟動的證據條件——蓋然性標準
證明標準決定了案件結果,也影響證明活動的開展。根據《監察法》第45條及《刑事訴訟法》176條、291條的規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認定職務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標準。這既是監察機關移送起訴的準則,也是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標準,又是審判機關認定事實的標準。在審前程序中就要求達到最高程度的證明,忽視了辦案人員對案件的“漸進性”認識和事實的主觀判斷性,不符合人類認識規律。學界關於刑事缺席審判證明標準的探討與爭論懸而未決。有學者認為,刑事缺席審判作為刑事訴訟程式的一種特殊程式,基於其設置目的與程式特點,其證明標準應當低於一般刑事案件,即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即可。⑧ 還有學者認為,缺席審判是對被告人辯護權和參與權的限制,為保證程式的正當性,應堅持法定證明標準,即“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⑨
檢察機關是啟動缺席審判的主體,發揮承前啟後的作用,肩負甄選案件的重任,兼顧打擊腐敗等犯罪和保障人權的雙重要求。缺席審判啟動的證據條件直接影響訴訟目的的實現。過高的標準會限制公訴權的行使,大量貪腐犯罪案件無法進入缺席審判程式。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場的情況下,監察機關獲取的證據是有限的。起訴的及時性要求決定了檢察機關向法院提起缺席審判時不可能擁有太多的證據,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達到審判所要求的標準過於苛刻。啟動缺席審判程式的證明標準應採用“蓋然性理由”,即檢察機關在已有證據基礎之上,根據經驗、理性確信被告人實施了擬指控的犯罪,該案交付法院審判定罪有較大的可能性即可。
2、法庭審判的證明要求——排除合理懷疑
內地《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2款對“證據確實、充分”的條件作出規定,即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情節均須查清,定罪標準為100%。“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如何操作,卻沒有明確的解釋,可能會因司法人員理解不一而導致適用差異。根據法律相關規定,缺席審判中被告人的近親屬具有獨立的上訴權,被告人到案後,對判決、裁定不服還可以要求法院重新審理。法院前後兩次審理都是根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作出裁判,若案件事實、證據的認定得出前後矛盾的結論,司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勢必大打折扣。對於逃到國(境)外貪污賄賂犯罪案件的被告人,也許監察機關在調查時就無法獲取被調查人的供述。在沒有被告人供述又不出席法庭質證的情形下,加大了案件認證的難度。而嚴苛且不易把握的證明標準,要求法院審判時做到確定無疑是不切實際的,勢必影響缺席審判程式的適用效果。故缺席審判應適用相對較高的定罪標準,即“排除合理懷疑”。《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和證據規則》將證明標準依可能性和確定性的不同程度劃分為九等:第一等是絕對確定,基於認識論的限制,認為這一標準是無法達到的;第二等為排除合理懷疑,是刑事案件定罪裁判的要求,也是訴訟證明最高的標準,被視為英美刑事證明標準經典表述。⑩所謂“排除合理懷疑”,不是排除一切懷疑,而是有理由的懷疑,是一個普通理性人憑藉日常生活經驗對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明智而審慎地產生懷疑,並非吹毛求疵、強詞奪理的懷疑,其意義在於基於一定根據的、具體的懷疑來排除確定性。同時,這一懷疑對於一個合乎理性的人來說,具有合理的接受性。法官在適用此標準時必須給出明確的具體的理由,裁判文書要有說理性,保障主觀證明標準的客觀性。
(二)不同訴訟主體的證明標準
基於“平等武裝”的理念,被告方居於天然弱勢地位,為實現司法公正並保障人權,根據不同證明主體確定不同的證明標準較為適宜。對享有一系列國家司法資源,又有取證能力較強的偵查機關的支持,代表國家進行公訴的檢察機關提出的犯罪事實適用嚴格的證明規則,並確立最高的標準,毫無爭議。儘管立法強化了不在案被告人的救濟手段,但在被告人缺位的情況下,辯護律師提出的有關事實主張、證據及其質證能力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故對其證明要求自然無法與公訴方相提並論。被告方承擔證明責任時,其司法證明程度達到高度可能即可。如辯護律師對案件證據非法性或在上訴程式中申請宣告一審法院存在違法審理等訴訟請求的,其只需提出證明使法官產生內心懷疑足矣。
刑事訴訟中,證明標準是貫穿整個刑事證明過程的一根金線,指引訴訟實踐,訴訟主體對證據進行收集、審查並判斷後做出裁判圍繞證明標準而展開。在不同訴訟階段,針對不同訴訟主體確立多元化的刑事缺席審判證明標準,既為跨界開展追贓活動正名,又能使潛逃至境外的貪污賄賂罪犯得到及時、公正處理,避免刑事缺席審判制度形同虛設。
參考文獻:
① 數據來源於《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關於部分外逃人員藏匿線索的公告》,中央紀委監察委網站。
② [意]切薩雷·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7頁。
③ 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編):《<關於修改中國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3頁。
④ 參見李浩:“證明標準新探”,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4期。
⑤ 趙琳琳:“我國刑事缺席審判程式的多維度探析”,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
⑥ 2021年3月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⑦ 參見袁義康:“證據法視野下的刑事缺席審判”,載《政治與法律》2019年第7期。
⑧ 參見胡志風:“刑事缺席審判中的證明標準”,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第26卷第3期。
⑨ 參見陳國慶:“刑事訴訟法修改與刑事檢察工作的新發展”,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
⑩ 參見《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和證據規則》,卞建林(譯),中國政法大出版社,1996年,第22頁。